

“可能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,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,骨折的风险非常大。有一个数据,65岁以上老年人在骨折之后一年内的死亡率,已经高达40%!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?因为骨折后老人动不了,无法活动,无法运动,就容易导致一些并发症,比如肺炎、血栓……导致这个人身体的衰老急剧加速,很快就去世了。
所以说,骨质疏松并不可怕,真正怕的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折。有些老年人在骨质疏松的过程中,骨头里产生了空洞,如果不及时干预,可能一个很小的外力刺激,就会引发骨折。
有很多老人是因为最后一次摔倒,而结束了生命。”

吕维加教授参与了中国骨科医学研究从无到有的全过程,他是国家科技进步奖得主,中国香港首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总负责人,连续10年被ISI评为全球Top1%科学家;他深度见证并参与了30年来中国香港的科技发展历程。作为骨科领域专家,他是香港大学医学院骨科实验室的创始人,也是香港生物学工程学会的创始主席,带领骨科研究实现多项从0到1的开拓与突破。
吕维加和马驰既是师徒,又是创业合伙人。马驰拥有香港大学骨科学博士与人工智能硕士的复合背景,曾获评福布斯2022年“30Under30”科技精英,现任博志生物科技首席执行官。
博志科技由吕维加于2018年联合创建,专注于用智能设备提升骨科领域的检测和治疗手段,拥有全球最精准的骨密度检测系统。

谈及愿景,吕维加提到:“《黄帝内经》中说,上医治未病。我们期望,老年骨空洞的治疗,也就是骨折的预防,有天能像打预防针一样,不会有风险,也没有很大的疼痛。”
吕维加和马驰师徒二人,在泉果无限对话,分享了他们在骨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,以下是分享内容精选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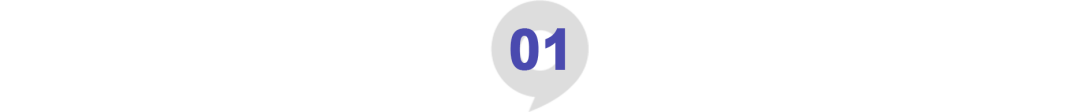
初心

“我最早学的是人工智能专业。吕教授招募我的时候说,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,但是在医学临床端,还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去改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用人工智能在骨科做新的创新,新的模式。”

吕维加教授
我从北京出发一路留学,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。上世纪90年代,差不多是94年左右,得益于梁智仁院士的人才招募计划,在这个契机下我来到了中国香港展开学术事业。当时中国香港正面临着要回归,对我来说,这是一个很令人激动的大环境,所以我这30年应该说是跟着中国香港一起风雨同舟,一路走来,起起伏伏。
*梁智仁:骨外科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,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,香港大学荣休教授、李嘉诚医学院矫型及创伤外科学系与生物化学系荣誉教授和前主任。

那时候内地和中国香港的骨科研究其实都尚未开展,梁院士是比较有创新精神的一个人,他到北美考察完之后,提出医学研究需要找些“专门做研究的人”。我就是当时他招募回来的“专门做研究的人”之一。
过去是怎么做研究呢?有很多现在已经很资深的医生们,当时都还年轻,就是自己养几只兔子,在上面做一些自己想做的研究。我们来了以后就说这样不行,研究前需要先有一个计划书,看看前人有没有做过,把想做的研究经过推算论证,看看预期结果,做研究要有一个规范的形式。从这一点来说,我们把骨科的研究,从临床医生的想法,真正变成了一个有计划、有规模的新兴模式。
1994年我刚回中国香港的时候,骨科只有我一个人,连一个学生都没有,到了现在,比如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骨科研究部门,已经有了四五十名研究人员的规模。再看咱们内地这边,比如瑞金医院、301医院、协和医院等等,都有了很大的团队。所以可以这样说,专业的骨科研究和临床结合的这种模式,是我们从北美带回了中国香港,再从中国香港进入了咱们内地。
马驰博士
我是2016年来到中国香港的,当时学的是人工智能专业。吕教授招募我的时候说,手机一代一代的都在迭代,比如说iphone,从10做到11,做到13,再做到15,每年它都有一些精确化的提升。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,都聚焦于我们日常生活,但是在医学临床端,还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去改进。比如说如何把一个疾病的诊断变得更加精准?如何把手术做到标准化?以及我们的耗材如何能够有更多的生物活性?在这些方向里,伴随着整个内地和中国香港骨科研究类的发展,我们在逐渐探究什么是未来的新模式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用人工智能在骨科做新的创新,新的模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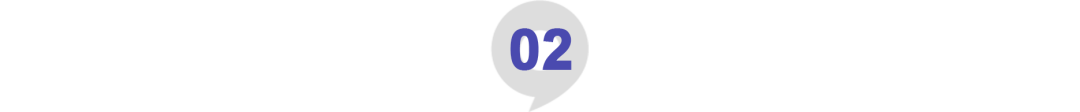
方法

“医生的知识与经验半径,有时甚至会决定患者一生的命运。”

吕维加教授
我90年代来到中国香港的时候,内地还是个年轻社会,而中国香港已经慢慢步入老年社会了。当时梁智仁院士是我们的主任,有一次他说,老年人的骨科手术里,钉子打进去,很快就脱落了,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打?我听他这样说,我就说,那咱们设一个计划,看能不能够找到最强的区域,也就是最强的一块骨头,往最强的这个地方打钉子。
大家可能认为,一个人全身的骨头都一样,其实我们用CT扫描进行分析,知道一个人身体不同部位的骨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,我们把患者骨密度最高和最低的地方给标志出来,然后找骨密度最高的地方打钉子,我发觉它可以让“beautiful手术”(漂亮手术)的比例提升30%。

什么叫beautiful手术呢?想象一个场景,医生早年拿个片子出来,说你看我这手术做的漂亮吧?钉子打的特别直,不用尺子量,就能打得那么好。这就是漂亮(beautiful)的手术。
可是梁院士说,在那个位置打,第二天钉子就脱出来了,宁肯钉子打的不“beautiful”,也要打的“strong”,他讲了一句话叫purchase the bone。我听了他讲了无数次,意思是钉子要真正的能把持住这个骨头,才能让内固定更牢固,或者让骨折的修复更牢固。
正是在这个理念的引导下,我们和当时第一军医大学的钟教授一起,联合一些医学同仁,一起把人体骨骼最强的这些部位都标注出来,但是由于当时技术的局限,我们只在尸体骨上标出来,但并不能在每个病人面前,实时地把最强的部位找出来。

经过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医疗技术的改进,今时今日,我们的团队就能把这个所谓的数字化科学真正融入到临床中去。简单来说,任何一个病人来了以后,做一个CT扫描,我们就可以把当年在尸体上找到最佳的骨密度位置用AI的模式找出来,这也是骨科手术打钉子最牢靠的最强点。
马驰博士
过去30年整个医疗界的改革,可以说也是一个科技进步的变革。我们用更好的,更先进的技术,可以把骨科诊断的精度从60%提高到99%。医生可以用更精准的数据来评估患者的骨折风险,从而去提前干预。
“可能很多年轻人并不了解,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,骨折的风险非常大。有一个数据,65岁以上老年人在骨折之后一年内的死亡率,已经高达40%!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?因为骨折后老人动不了,无法活动,无法运动,就容易导致一些并发症,比如肺炎、血栓……导致这个人身体的衰老急剧加速,很快就去世了。
所以说,骨质疏松并不可怕,真正怕的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折。有些老年人在骨质疏松的过程中,骨头里产生了空洞,如果不及时干预,可能一个很小的外力刺激,就会引发骨折。
吕维加教授
根据我们最新的发现,有些人的骨质疏松是系统化(systematic)的,这种情况下不用怕,你正常生活,这种系统化的骨质疏松就像我们头发变白了,皮肤变皱了,不用特别担心。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在骨质疏松的过程中,骨头里产生了空洞。就好像几年前,中国香港有个很大的台风,很多老树一吹就倒了,打开来一看,里面有很多虫洞。
骨头也是一样,假如没有什么空洞的话,可能骨折风险不会那么大。一旦骨柱之中有空洞,你可能在做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的时候,受到很小的外力刺激,就会引发骨折,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风险。但是在医疗上面,目前并没有解决的方案。因为,首先你要能识别这些空洞;第二你要有能力治疗这些空洞。

目前医学界比较常用的是用名叫DEXA的设备来测量人体的骨质疏松情况。但发现,如果老人超过60岁,测量出来的数据,可能并不准确。
DEXA的主要测试方法,就是从腰上面拿三个腰椎骨来进行测试,从而得出你的骨质疏松情况。在60岁以前,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老年人的骨头都还健康。但随着老人的年纪逐步增大,随着骨质增生越来越严重,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。
什么原因呢?是因为DEXA是把你所有测试的骨头都算进来,做个平均数。那骨质增生部分的骨头,虽然对我们的骨强度没有多大作用,但DEXA会把这些数据也算进来,可能结论你的骨骼很健康。但实际上,你骨骼可能有空洞,也因此有很高的骨折风险。
这是目前在骨检测领域的一个痛点。
马驰博士
玛丽医院是早期香港大学的教学医院,引进了我们最新的技术叫QCT检测,也是新一代的骨质量检测。
吕维加教授
OCT采用了一种我们名为自体模的技术,马驰非常深入地参与在这个算法中。所谓自体模,就是说无需外来的体膜来做校正,而是用自身校正,把每个人的骨骼特点计算出来。自体模技术让我们可以全方位检测你全身的230多块骨头,当然我们重点想了解的就是负责人体承重的50多块骨头,包括大约20多块脊柱,以及下肢的承重的骨结构。
接下来我们用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科学计算,在发现你的骨骼有空洞后,我们就会进行风险因子的评估。如果这个风险因子超过了某个安全数值,你可能出门不小心摔个跤就会骨折,我们就要看能不能够在没有骨折的情况下用一套模式来进行干预。这是预防治疗。
方法层面,目前大家知道在骨折之后,医生会用骨水泥进行微创的填补。受此启发,我们希望在未来,能够用骨凝胶去填补空洞。用很细的针将一种新型材料打进去,这种材料打进去时是很稀释的液体,通过某种技术,比如说光照等等,马上让它变成一个很强硬的材料,在体内把空洞都给填补上。
马驰博士
还有一种方法,就是用局部的补孔洞的载药凝胶,通过药物释放去强化我们的骨骼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在我们60、70岁的时候,通过我们的凝胶载药,可以去加强你成倍的骨骼的承载力,你就可以变成一个“不倒翁”了,即使摔倒你也不怕。
具体说说这种凝胶类的药物。传统的材料学家一直想去模拟我们的人骨,但我们人类的骨骼是几千年进化出来的一个结果,很难在体外去进行模拟。我们第一代的骨材料叫骨水泥材料,是在国外由Hammer教授提出的,已经垄断了有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。
但这种传统的骨水泥材料的力学强度太强。它就像塑料一样,比我们人类骨骼强大概十倍。它会逐渐把我们老年的骨头磨损,压迫、压骨折,所以其实长期很难和人体去进行一个高度的相融。

吕维加教授率先在国内开展研究的这种骨凝胶,就是要突破美国人的卡脖子技术。在2019年,吕教授拿到了中国药监局第一张脊柱骨密度的骨水泥注册证。我们这种新一代的凝胶材料把强度降低到了五到十兆帕,跟我们真正人类的骨骼是天然吻合的,所以它能够进行局部骨填充以及药物的释放。
人的衰老是必然发生的。60岁以上老人发生骨质疏松的比率已经超过了30%,中国有将近一个亿的骨质疏松患者,每年有将近300万人因为骨折对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现在一年内,60岁以上老人因为骨折的死亡率已经接近20%,致残率已经接近50%。
很多人因为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摔倒,结束了生命。
吕教授经常和我说,医生的知识与经验半径,有时甚至会决定患者一生的命运。我们想顺应时代的发展,把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融入到医生的诊疗体系范围内。通过AI和大数据,医生可以获得数以万计的诊疗经验,极大地拓展经验半径,在面对患者时,给出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。

彩蛋:吕维加谈香港科技发展
中国香港如何从科技沙漠,到科技独角兽的高发地?
自从1994年回到中国香港之后,吕维加参与了中国香港科技领域30多年的发展,他总结中国香港科技的发展,得益于三个视角:
吕维加教授
不只是医学研究领域,那时候整个中国香港的科技发展,都可以说是一片沙漠,没有文化资源,也没有工业资源……为什么现在成为了一个高密度诞生科技企业独角兽的地方?我个人总结了三点原因:
第一,人才。要把沙漠变成绿洲,第一件事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,广泛招募各种各样的研究人才;
第二,好的机制。提到机制首先的是管理机制,在管理中要对人才有充分的信任;
第三,给人才充分的自由度,这一点很重要。创新是不能被指定的,并不是把所有计划书写好,经费定好,目标设定好,创新就出来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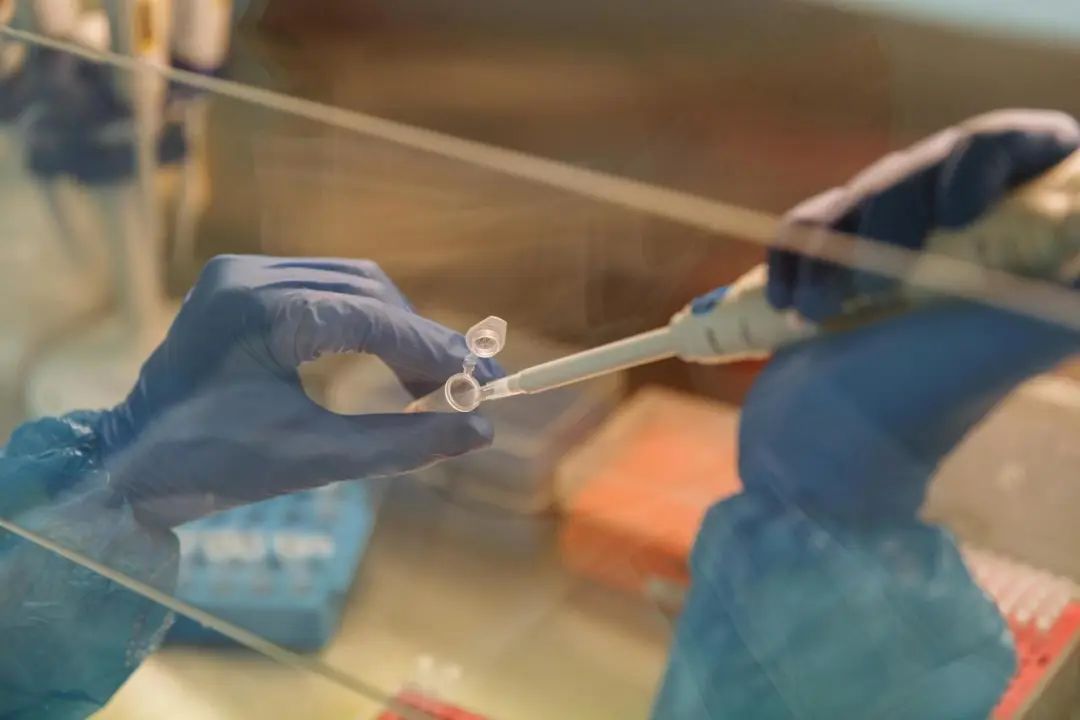
科学面前是平等、是真实。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人都能做一个独角兽出来或都有重大突破,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中国香港的大学也好,科技园也好,每一个新来的员工,都会给他一个安稳的项目,慢慢精雕细琢,并不强制要求马上出什么有影响力的文章。有新的想法很好,实在没有,就把一两个实验做扎实。
人才,机制,自由度,有了这三样东西,自然而然会有更多的创新涌现。


泉果博物馆
《混凝土风暴》
CONCRETE STORM
增强现实(AR)艺术装置
2007年
艺术家:Studio Drift
Lonneke Gordijn & Ralph Nauta
增强现实艺术装置《混凝土风暴》诞生于荷兰艺术工作室Studio Drift。两位创始人Ralph Nauta和Lonneke Gordijn,被称为“链接科技与仿生学的二人组”,作品曾入选荷兰国家博物馆的永久收藏。
Studio Drift擅长从自然与生物的潜在机制中学习,通过结构、交互和创新,创造出科技、自然与艺术深度交融的空间。
他们在采访中提到:“我们仍在努力实现童年的幻想,从自然中攫取灵感,融合技术做出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东西,这就是创造力的意义所在。”
2024-03-10 20: 59
2024-03-10 20: 58
2024-03-08 19: 55
2024-03-08 19: 55
2024-03-08 19: 55
2024-03-08 15: 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