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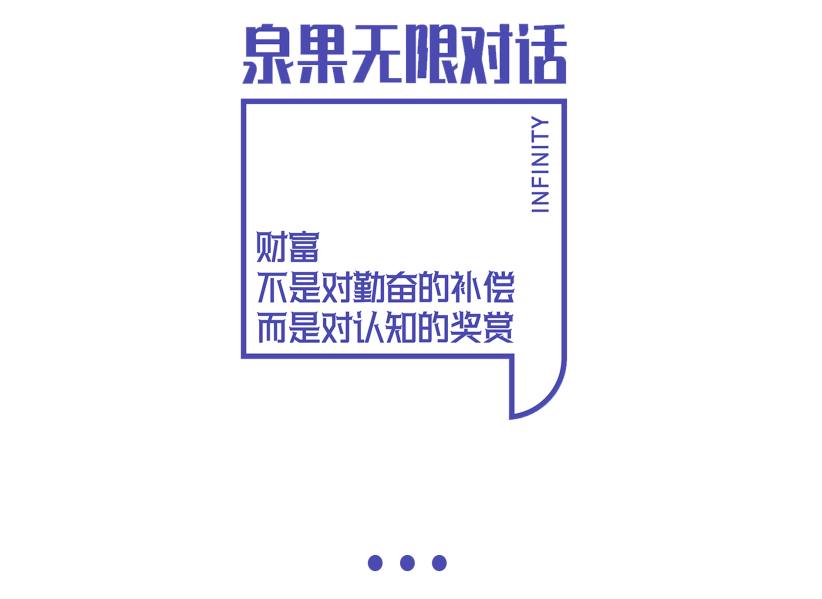
■ 刚创业时,跟10个客户推荐云端软件,只有2个会被说服,考虑使用,其他人会认为本地更便宜、云端不安全;今年,我们做了一个统计,10个客户里,有3个会主动要求数据上云。我们在个人生活中也在使用云端服务,看到了它的安全性与优势......透过这种变化,我觉得中国比美国会经历更快速的软件价值认知改变。
■ 我觉得中国软件仍在初始化阶段。这中间需要一些创新,不是单纯的软件,而是“软件+其他”。我们可能要并行很多条路,需要有真正能够抽象出客户需求的产品经理,让用户有更多的价值获得感,才能走得更长远。
■ 还有一个观点,可能未必所有人都认同。我认为在中国创业,很大的一个故事就是从农村包围城市。在SaaS领域和软件领域,尤其在寒冬时期,做大项目的公司,客户缩减预算、账期长……面临非常深刻的打击。反而是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的公司,展现出了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。
■ 大企业在自己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,如果能更有前瞻性,带动上游的一级、二级、三级供应商变得更加数字化,这比单点工厂的降本,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提升。
以上是黑湖科技创始人周宇翔在【泉果无限对话】的分享与研判。
周宇翔以最高荣誉毕业于美国常青藤学校达特茅斯学院,是大数据和工业软件领域的连续创业者,曾入选《财富》杂志中国“40 under 40”商界精英榜单。
周宇翔毕业后在投行做并购投资项目,接触到大量国内外制造业企业。在一次跨国并购项目中,他们要收购一家财务上已经濒临崩溃的德国制造工厂,但他观察到:要收购的这家德国工厂,虽然已经深陷财务危机,但生产管理的软性能力非常好,依然能做到所有的产线数据由机器采集并实时传输到电脑,完全基于数据发现和解决问题;相比之下,中国的工厂是“走动式管理”,无论多么先进,都需要管理者在一线来回走动观察,通过这种方式系统性管理车间;也是通过这个对比,他意识到,即使中国制造业已经位居全球首位,但依然存在着效率上大量的提升空间。
“终究有一天我们要跟上这个脚步,未必是同样的路径,但一定要达到科学管理。”
这也成为了黑湖科技一直专注的领域——帮助制造业打通企业内外的数据孤岛,系统性地提升效率和工业协同性。目前,黑湖科技已经拥有包括农夫山泉、蜜雪冰城、华光集团、老凤祥在内的近3万家制造企业客户,覆盖食品、饮料、家电、汽车、化工等行业。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数据被采集、流转、挖掘后,显示出了巨大的价值。
周宇翔基于已经服务过的近3万家制造业企业所积累的海量数据和一线案例,分享了他们是如何让数据驱动制造业工厂的;并从创业历程中的迭代与进化,以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的观察者的视角,分享了对中国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的思考。


以下为周宇翔分享实录精选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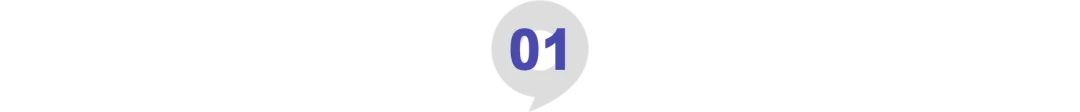
工业软件
在中国还走得通吗?
创立黑湖之初,我曾经到一家化妆品包材厂打工,和一线工人们一起待了好几个月。
这家工厂主要是给欧美大牌做包装代工的,接的单子都很大,一个SKU可以给到几十万件,然后就三班倒,昼夜不停地做。但这些工厂被视为大牌供应链上的廉价产能,毛利率非常低。
当时,一些日韩和国产的小众品牌开始火了。因为它们的用户群体非常细分,SKU数量非常多,但单一SKU可能只有几千件试产,如果某一款卖得好,再翻单。这些小众品牌愿意付两倍甚至更高的毛利。工厂也希望能多承接一些毛利更高的定制化订单。
我工作的车间主要接触的就是这些订单。过程中,我发现了一个问题:以前大单的生产方式是连着生产二三十天,然后停产一天切换产线;现在每个订单的量少了,车间生产六个小时就完成了,但要停五到六个小时才能切换到新产线。过程中还有五六个工种要协同配合,工人们都是凭着经验做事,掐秒表算下来,真正有效的作业时间不到一个小时。
这意味着,虽然毛利提高了,但整个生产产能的利用效率急剧降低。

我们就想,是否可以把以前通过经验来协作的方式,变成一个简单的APP,提高协作效率?
所以黑湖第一版产品的理念就是“车间现场的微信”。但不同于微信的非结构化聊天,我们希望它有任务机制,形成结构化的信息,基于角色和前后条件等来触发任务。这样工人就能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安排,而不是靠自己的经验和信息作业。
我们在两周内搞出了一版粗糙的产品,进行对照测试:生产一个品类的两条产线,一条产线用我们的APP相互协作,另一条按照原始方式作业。
试跑了三周后,反而是没有装APP的工人先找到我们,问他们能不能也加入试用。我们觉得很惊讶,因为正常一个管理系统,一般员工都会比较抵触,为什么他们却想主动试用?询问后发现,工厂是计件工资,工人虽然吐槽APP消耗流量等,但他们的等待时间缩短了。以前需要五六个小时切换产线,现在两小时就搞定了。一个月下来能多赚大几百块钱,所以他们有很强的意愿使用我们的产品。
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,让我们看到了产品的价值所在。
我们最早的客户,很多都是江浙沪的“厂二代”。这一代人相信数据、追求客观,不信奉经验主义,我们正好一拍即合。在客户的加持下,我们就快速地做实验,发布了第一款产品“黑湖智造”。早期的一些免费客户也转为了付费的客户,客户也拓展到了很多超大型企业。

后来我们回顾这事儿,当时SaaS在中国完全走不通,华为和阿里在C端做了一些云服务,也完全没有进入到B端,没有人看好工业软件被云化。
为什么我们坚持下来了?我觉得有以下几点:
第一,吸取之前创业的经验,产品一定不能闭门造车,开发几个月才拿去测试。我们需要快速测试产品是不是符合客户的需求,给他们带来价值感。所以在两个星期内快速搞出一个系统,并且部署在云端,在客户的加持下,实现了快速迭代完善。
第二,基于手机这类移动端设备实现低成本落地,不用客户去重新购买硬件做嵌入式改造开发。
第三,引入了微服务架构。不用每次服务新客户都从零到一去定制写代码,也不是定制开发一个僵硬的系统,而是把代码封装成了一个微服务,可以像搭建乐高积木一样,贴合用户的流程,快速部署服务,新需求、新组件的开发也更加敏捷高效。

2020年以前,大家都在投SaaS、工业互联网,而现在市场极度倾向另一端。
我认为,SaaS和软件在中国仍然有价值,仍然有大量的需求未被满足。
但这中间需要一些创新,不是单纯的软件,而是“软件+其他”。
美国有家公司叫Toast,它一开始是给餐馆提供小工单服务,比如点菜、库存管理等,后来却变成供应链金融公司,为餐饮业提供支付、贷款等业务。
我看到中国也有许多企业在进行类似的创新。我们可能要并行很多条路,需要有真正能够抽象出客户需求的产品经理,让用户有更多的价值获得感,才能走得更长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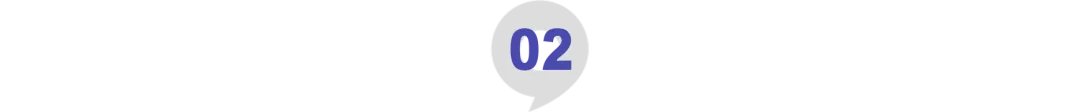
在中国创业
很大的一个故事就是
从农村包围城市
2020年,企业复工复产期间存在一些困难。于是我们就响应号召,推出了一个公益政策:所有为抗疫做出贡献的企业,我们可以把黑湖智造的系统对他们免费开放两年。有100多家企业都接入了系统。
一些小企业用了一段时间后,跟我们吐槽说,4、5个月系统都没跑通。我们复盘发现,在大企业才有协同的命题,因为他们有很多流程与部门,生产相对规范,所以系统服务能跑通。
但对小企业而言,几乎没有规范协同这个概念。我们曾经去拜访一家口罩厂,一大早就到了,老板指着桌上一叠厚厚的纸单说,这是我们每日的工单,谁来得早谁就能领到最好的单子,然后认领一个机器,去仓库取物料,守着机器生产,晚上结算。他说,用我们的系统,工人报个工要点好几次,搞了半天是自己在和自己协同。
整个产品的设计理念确实不适合小企业。但我们履行承诺,工厂如果要继续使用,我们仍然免费给他们用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们的工程师在整理数据库时,发现有几十家当年参与试用的小企业,在以一种非常“诡异”的方式使用系统——我们是一个协同系统,正常来说,一家公司开了几千个账号,每个账号每天都会有互相的操作和活跃度。但这些工厂,我们给他们开了四五十个账号,只有3、4个账号每天高活跃,活跃度甚至高于那些大企业账号的最高活跃度。
于是我们去回访这些工厂。结果发现,他们的使用场景,完全超出了我们原本的设想:
第一个场景,答复客户进度。这些小工厂接的单子都非常零散,每个单子的数量很少。以前客户询问交货进度,他们没法给出准确的答复,可能明天交付的单子还没开始做,三天后交付的单子却已经做完了。现在他们用系统来追踪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进度,这样就能高效安排生产,准确回复客户。
第二个场景,准确结算工资。很有意思,小工厂的“CFO”通常就是老板娘,负责算账和发工资。每到月末,工人们会有一个小本本记着这个月计件计时的工资,但有时候和老板记的对不上。老板娘现在会指定一个工头来每天帮工人在系统中录数,结算的时候就能完全对得上,不用再扯皮了。
第三个场景,产业集群协作。当时很多国外的订单涌到中国来,导致小工厂产能过度饱和。但中国的一个特点是,每个街镇都有产业集群,所以当订单过剩时,他们会跟周边的工厂协作加工。以前相互之间打电话、发微信,信息同步容易出问题。现在,他们也要求协作工厂开一个黑湖账号,用系统报工。

我们觉得很有价值,干脆去孵化一个新的东西,因此诞生了“黑湖小工单”。小工单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的意义和价值——不只是在大客户那边做一些项目。
当时开发新产品时,员工问我有什么要求,我说我只有两个条件:
第一,交付时间必须要快。
黑湖智造通过微服务的搭建方式,把以前平均需要九个月时间交付的信息化项目缩短到两三个月。
但两三个月对于小工厂来说,还是太长了,我们决定三天之内必须交付;工厂要能快速上手会用,甚至不需要下载APP,在小程序、企业微信、飞书上就能使用。
第二,定价必须极致便宜。
黑湖智造是按照账号数量、订阅时长、功能订阅数等来算费用,价格在十万到上千万不等。虽然比起买断式的软件,报价已经是其十分之一,但这对于小微工厂来说还是太贵了。
小工单是如何定价的?
我们访谈了几家工厂,录入员的平均月薪是7000-8000,所以小工单第一版基础版的定价就定在了每年万元左右。在中国,没有任何软件卖到这个水平,但这击中了小微工厂的需求点,只需要一个月就能算得过账来。如果再高,工厂就会犹豫。
但也有很多时候,工厂未必真的是算财务账,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产品,只要能够精准解决了用户的某个痛点,让老板不再头疼,就够了。
当然,其中潜在的价值未必能够立刻感知到,软件带来的效益提升很难在财务数据上精准量化。从感性角度来说,它提供的安全感、数据引发思考与行动,不同的企业有很大差异。

小工单的销售模式也很有意思。
小工单的销售不是西装革履拿着电脑的人,很大一部分是外卖小哥,都非常年轻,二十五六岁。
他们去到不同的城市,去往不同的产业园区,争取和老板见面的机会。他们在销售的路上可以说是“斗智斗勇”:有的销售小哥去到工厂园区,还会碰到园区的看门狗,所以他们可能得一手拿着平板演示系统,一手带着板砖或者宠物零食……基本上见到10个老板,8个会把他们轰出来,剩下2人听他说5分钟,可能有1个会允许二次拜访,转化为我们的潜在客户。
前25%的销售每个月能赚到十万左右,因为他转化客户能力特别强,但是也非常辛苦。
我去年分享这个故事时,大家很惊讶。但其实,中国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强的地推文化,最早就是在工业,然后到了服务业,现在又回到工业。

2021年3月问世后,迄今为止吸引了25000多家中小工厂。但全国的中小工厂数量大约是250万家,我们目前的占有率连1%都不到。这些小微企业非常渴望进步和更好地发展,但很少有人去服务这个群体。
我觉得这些小微工厂构成了我们未来新质生产力的重点,而不只是那些大型企业。
在美国,Salesforce等这些大公司,都是头部客户贡献了最大的营收,基本上不做小微企业这个市场。
而中国很多的创业故事都是“从农村包围城市”,包括现在很多行业都在追求下沉,从淘宝最开始的成功,到后来拼多多的成功,都可见端倪。
我觉得在中国,下沉小微企业反而是更好的选择。尤其是在寒冬时期,软件和SaaS领域,做大项目的公司,客户缩减预算、账期长……面临非常深刻的打击。反而是定位于服务小微企业的公司,展现出了更强的韧性和生命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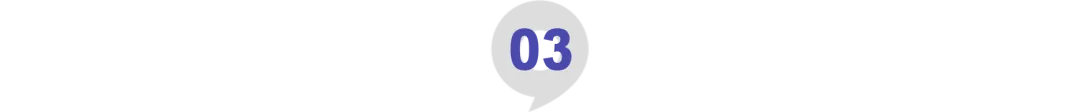
供应链的数字化
比单点降本更能增效
最近两年,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变化。
一些大型企业找到我们,说意外发现自己的供应商在用黑湖的产品。他们很惊讶,因为过去一直专注于自己的数字化,但是经常会因为和供应商在信息协同上的阻碍,影响到自己的生产效率。过去很多年,他们一直在不断说服供应链上游的工厂做数字化,搞补贴、做培训,甚至在采购中提要求,但最后都难以推动。
结果他们意外发现这些工厂自掏腰包买了我们的软件,所以他们想找我们谈合作,是否能在用户授权下把部分数据开放给他们的系统接通,这样整个供应链的协作就变得很动态了。
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。
企业自己发展数字化的基础上,能否要有前瞻性?带动上游的一级、二级、三级供应商变得更加数字化。这种效率提升比单点工厂的效率提升带来的成本节约、能源节约更有作用。

我们孵化了黑湖供应链的新产品。它比起这两款传统软件更像一个协议,它像数据,我们运用了区块链、隐私计算等新技术,打通供应链。小工单的系统向下游企业开放权限,形成一条动态的链接。
谈到供应链,最近几年有很多中国的产能,尤其是比较偏上游的,迁移到东南亚一些地方。疫情后,我去了三四趟东南亚,包括菲律宾等地,我发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。
有一家黑湖的客户,给运动品牌造袜子的,把所有产能从佛山转到了越南。但是他去了以后,发现几个严重的问题。第一,看似工资很便宜,实际上工人的有效工时不够;第二,基建有问题,经常漏发或延误,还有的地方会停电,有点像东莞30年前经历的发展阶段。
这家企业算了总成本,发现虽然工资便宜、关税低,但一抵消,某些产品线还是得放在中国,比如需要加入银线的高端产品等。所以他又关闭了一些越南工厂,又租回原本在佛山的厂房,准备重新启动。
制造业的产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能力,上下游的供应商都要有更强的协同能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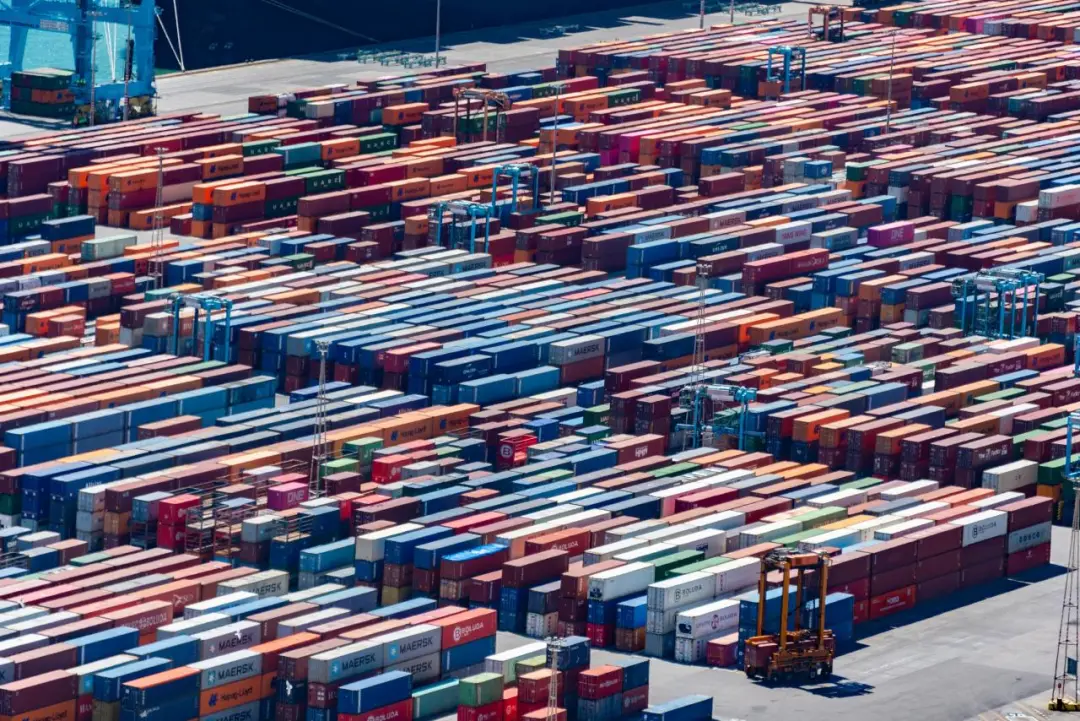

通过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在特定产业中的经验,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处在中国软件的初始化阶段,可能得在五年以后,才能回头总结出过去十年中国软件和软件市场的特点。
目前来看,国家的政策和各种会议精神,民间的各种认知和声音,我们对数字化的热情,高于任何一个国家。
从我们自己的数据来看,刚创业时,跟10个客户推荐云端软件,只有2个会被说服,考虑使用,其他人会认为本地更便宜、云端不安全;今年,我们做了一个统计,10个客户里,有3个会主动要求数据上云。我们在个人生活中也在使用云端服务,看到了它的安全性与优势……透过这种变化,我觉得中国比美国会经历更快速的软件价值认知改变。

2024-08-27 10: 39
2024-08-27 10: 39
2024-08-27 10: 39
2024-08-27 10: 39
2024-08-27 10: 39
2024-08-27 10: 39